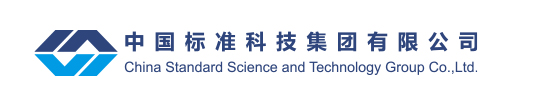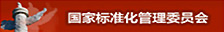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競爭政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競爭法是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核心實現機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政策是國家為保護和促進市場競爭而實施的一項基本的經濟政策,其核心目標是通過保護和促進市場競爭,確保競爭機制發揮作用,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增進消費者福利。這種廣義上的競爭政策既包括狹義上的競爭政策即競爭法律(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也包括旨在促進國內經濟競爭自由和市場開放的各項政策措施。
從理論上來講,相對于其他經濟政策,競爭政策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項基礎甚至是優先的經濟政策,這是由市場經濟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而從現實來講,競爭政策在我國以往的很長時間里并不被重視,尤其是相對于產業政策來說。但從2015年以來,從“逐步確立”到“強化”,從“基礎性地位”到“基礎地位”,競爭政策在我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其地位日益得到提高。2022年修改反壟斷法時,“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正式“入法”。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包含公平競爭在內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可以說,競爭政策已經提升到我國的頂層設計的高度。
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需要通過相應的機制和路徑去實現的。一般來說,這些機制和路徑大體上包括制定和實施競爭法(包括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實行競爭中性原則、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以及積極進行競爭倡導等。其中,制定和實施競爭法是核心,開展競爭倡導是為實施競爭法和實現廣義競爭政策目標提供文化基礎,而實行競爭中性原則和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則是在競爭法之外的重要制度性措施,這兩者雖然不屬于競爭法本身,但應是競爭法貫徹和體現的基本原則和理念,對于確立和實現廣義的競爭政策來說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都已經實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前者確認和保障各類經營主體有著公平競爭的整體市場環境,后者則以公平競爭的標準去衡量和修正政府的其他經濟政策,從而非常明顯地體現了競爭政策的基礎乃至優先的地位,意義非常重大。
雖然廣義上的競爭政策不限于競爭法,但競爭法無疑是競爭政策的核心。作為競爭政策的核心,競爭法通常包括兩部分,即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因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產生的破壞競爭的力量或者作為市場競爭“副產品”,主要表現為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前者使競爭開展不起來,后者使競爭無序發展。無論是壟斷行為還是不正當競爭行為,都使得競爭的積極作用不能正常發揮,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破壞,經濟的活力受到抑制,因此都要受到相應的法律規制,這樣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都不可缺少。
在實行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并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及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我國相應地產生了從法律上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要求,并逐步形成了若干競爭法律規范。早在1980年10月,國務院就頒布了《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首次提出了反壟斷的任務。此后,國家有關法規、法規性文件和規章中又對相應領域內的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問題作了一些零星規定。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標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市場競爭機制的地位和作用更為重要,從法律上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的要求也更為迫切。經過多次的名稱改變和內容的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終于在1993年9月2日通過,自1993年12月1日起實施。為了增強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可操作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發布了一系列行政規章,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作了細化、補充和發展。另外,許多省、市、自治區、經濟特區、省轄市以及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先后頒布了地方性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或者規章。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2日發布了《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該法在2017年11月4日和2019年4月23日分別經過了修訂和修正,相關制度在不斷完善。在反壟斷法方面,經過長達近13年多的反復醞釀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終于在2007年8月30日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該法在2022年6月24日經過了重要的修改,制度規則進一步完善。我國形成了由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共同構成的競爭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為確立和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中具有不同的特點
從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來看,競爭法通常由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兩個核心部分構成,盡管有的法域是分別制定兩部法律,而有的法域制定了包含二者內容的一部法律,還有的法域在成文法方面以反壟斷法為主,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體現在判例法和其他相關法律中。總體來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是旨在禁止以違反商業道德等不正當手段從事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的法,而反壟斷法是旨在反對限制競爭、維護自由公平競爭和經濟活力的法。作為競爭法的兩個基本組成部分,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這兩者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方面有著不同特點。
首先,產生的背景與法律淵源不同。不正當競爭行為在簡單商品經濟時代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就產生和存在,因此在古羅馬法上就已經有一些針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中和早期的普通法上也有針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定。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多種法律表現形式,既有專門的成文法,也有判例法和民法中關于侵權行為的規定等,其規定和適用主要針對較為具體的侵權行為。而壟斷行為或者限制競爭行為則主要是在壟斷資本主義產生之后出現的,是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因此反壟斷法的產生時間要晚于廣泛意義上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主要表現為專門的成文法,其規定和適用的靈活性和政策性更強。不過,作為現代第一部現代成文的反不正當競爭法(1896年的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第一部反壟斷法(1890年的美國《謝爾曼法》)的產生時間大致相同。
其次,規制的目的和側重點不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目的是防止競爭過度,消除惡性競爭的影響,主要是保障具體交易場合特定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側重維護微觀的競爭秩序,追求局部和個案的公正,保障靜態的財產權和人身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經濟領域的侵權法。而反壟斷法的目的則是防止競爭不足,保護競爭機制本身不受扭曲,競爭不被排除、限制,主要是維護宏觀的競爭秩序,側重追求整體和宏觀的效率,實現動態的交易安全。如果說反不正當競爭法側重維護公平競爭,那么反壟斷法側重于維護自由競爭。
再次,規制對象的性質和違法的構成不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是不正當競爭行為,這種行為在性質上是違反商業道德的,在分析時只存在是否構成的問題,而不存在適用除外和豁免的問題。而反壟斷法所規制的既包括壟斷行為,也包括壟斷狀態,而且壟斷行為也大多是結構性壟斷行為,這種行為的違法性一般不直接涉及商業道德,而且具有相對性和動態性,在分析時往往根據不同情形分別采取本身違法原則和合理原則,需要大量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并存在適用除外和豁免的問題。
最后,規制方法與責任形式不同。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事后規制,以民事制裁(主要靠私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手段為主,輔以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手段。而反壟斷法則既有事前規制,如調查市場結構情況和對經營者集中進行事前審查等,也有事后規制,以行政制裁手段為主,輔以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手段,并且救濟措施既有行為性的,也有結構性的,如分拆大企業或者責令實施合并的企業恢復到并購前的狀態等。因此,反壟斷法較之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更多的公法因素。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視
由于反壟斷法涉及的通常是全局性、宏觀性的問題,政策性更強,與整體的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息息相關,在西方一些國家甚至被稱為“經濟憲法”。但是,這并不是說反不正當競爭法就不重要,相反,其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兩者在保護競爭上有著共同的取向和積極作用,它們都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規制,都有利于維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對維護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來說,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兩者在功能上是相互補充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維護公平競爭秩序要以競爭能夠自由展開為條件,這就需要反壟斷法發揮其功能;而反壟斷法維護自由競爭秩序也需要公平競爭的環境,否則,自由競爭就會成為惡性競爭。此外,兩者在內容上還相互交叉,這主要是反壟斷法中的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制度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制度存在一些重合之處。因此,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甚至采取反不正當競爭與反壟斷的合并立法,并由統一的執法機構負責執行。實際上,即使我國采取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分別立法的模式,但是在兩者的具體內容方面還是存在交叉的地方,有時難以截然分開。例如,反壟斷法第三章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實際上也有明顯的不正當行為的性質;又如,在2017年修訂前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就有5種屬于壟斷行為;再如,雖然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時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條款最終沒有增加進去,但是2019年1月1日實施的電子商務法第35條實際上規定的就是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而這屬于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之間的一種行為。
另一方面,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方面有其特點和優勢,能夠更多地體現公平競爭的政策目標;而且,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適用的門檻相對較低,適用的場合就比反壟斷法要多很多,在實現競爭政策目標中同樣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對于近年來互聯網平臺實施的“二選一”等違法行為,市場監管總局除了從反壟斷法的角度進行查處外,也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角度進行了查處。
因此,在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背景下,需要充分認識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斷加強和改進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實際上,在國務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中一直是強調“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并將其作為強化競爭政策實施的重要舉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加大執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也明確提出:“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提升市場綜合監管能力。”可見,在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中,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都是并提的,兩者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即使是在2020年底強調“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相關政策文件中仍然同樣重視反不正當競爭工作的。2020年12月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2021年1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也提出“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國務院《“十四五”市場監管現代化規劃》多次提到“統籌提升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能力”,“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協同”。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過去五年工作回顧中也明確提到“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這說明黨中央、國務院在重視反壟斷工作的同時,也同樣重視反不正當競爭工作的,并且根據當前經濟社會形勢變化,對反不正當競爭進行了新的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
總之,與反壟斷一樣,反不正當競爭工作事關長遠、事關全局,意義重大。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涉及面廣,問題復雜問題,因此2017年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條規定除了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還明確“國務院建立反不正當競爭工作協調機制,研究決定反不正當競爭重大政策,協調處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重大問題。”這也進一步體現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競爭政策目標實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王先林)
來源網址:https://www.samr.gov.cn/xw/mtjj/art/2023/art_321af619df004316aa465ff642e96650.html